浑河之战中,戚家军为何全军覆没
天启元年,明军与后金的八旗军在浑河边上决一死战,此战以明军失败告终,戚家军亦在这一战中全军覆没。
要知道,戚家军素以百胜之师闻名,这支军队自明朝中期建立,从南打到北,上百次战役中未尝一败。为何浑河之战中,戚家军就全军覆没了呢,难道是八旗军真的太无敌了吗?

明朝末年,八旗军的强悍毋庸置疑,毕竟“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说法摆在那里。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浑河之战中戚家军的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敌八旗军。正相反,这支明军给予八旗军以重创,若不是明军主将袁应泰指挥无能,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1621年3月,在沈阳城下浑河南岸一场血战即将落下了帷幕。戚家军主将戚金一边高唱着军歌,一边孤身一人向满洲铁骑发起了决死冲锋:“万众一心,惟忠与义。气冲斗牛,敢赴水火……上报天子,下救黎民。”
1559年,戚继光组建新军。东南灭倭,北战蒙骑,百战百胜,打出了赫赫威名。唯浑河一战,戚家军终成绝唱!
假如支援的3万生力军能再前进10里;假如被俘的明军火炮手宁死不屈;假如戚家军火器充足……可惜没有假如,历史展现出来的,只有悲壮和叹惜。
戚家军自明朝中期建立,从南打到北未尝一败,为何浑河之战就全军覆没了呢?实际上,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队友太无能!

1618年,后金太祖努尔哈赤宣告“七大恨”起兵反明。相继攻占抚顺、清河等军事重镇,沈阳危急。明神宗不得不下旨从川、浙等省,抽调精锐大军增援辽东。
1619年,萨尔浒之战爆发。此战,努尔哈赤以弱胜强歼灭明军近5万人,大明将领陨落300余人。从此,明金攻守易势。
1621年,趁着大明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免职,巡抚袁应泰无法统筹全局之际,努尔哈赤挥师猛攻沈阳城。
沈阳危在旦夕,一支由川、浙精兵联合组建的援辽大军已经推进到浑河岸边。川军是秦良玉派来的4000忠州石柱土司兵(白杆兵),主将是秦邦屏。浙军是按照戚继光练兵之法训练的3000东南子弟兵,主将是戚继光侄子戚金。

原本,这支援军想与沈阳守军里应外合,夹击围城的八旗兵。可事与愿违,援军还没赶到沈阳城下,就收到沈阳刚刚陷落的战报。
这支军队从大将到士卒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众将一合计,决定立南北两营与八旗兵决一死战。
川军白杆兵悍不畏死,士卒们身披铁甲,腰挎大刀,手持竹矛,士气高昂的渡河布阵。为的是给留在南岸的戚家军,有充足时间列置车阵。(戚继光对付蒙古骑兵的战阵,火器兵在内,外围是一圈偏厢车)
一开始,努尔哈赤根本瞧不起这支川军,他直接下令让正白、正黄两旗精锐巴甲喇军骑兵冲锋。
一、战前阴霾
严格来讲,说浑河之战中的南军是戚家军也可以,但由于戚继光早已去世,这支南军主要是以戚家军为骨干组成的,所以称为浙军更为合理。
浑河一役,明军中主要有三支力量,它们分别是来自四川的白杆军、来自江浙的浙军和来自于辽东的辽军。
这三支军队全都是明军的精锐。白杆军是女中豪杰秦良玉所部,他们久经沙场,战无不胜,称霸西南;浙军继承自戚家军,战法先进,火器充足,训练有素,战斗力十分强悍;辽东铁骑纵横于北方,为李成梁所部,过去就连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人,也只是辽东铁骑的“家奴”。
所以,这一战,明军信心十足。
可是,明军中存在着巨大的隐患,那就是三军不和。

浙军与辽军素来因为朝廷的倚重问题而互相嫉恨,援朝时浙军夺得首功,与辽军再一次结下梁子,辽军还曾冤杀数千浙军,所以两军互相视对方为死仇。川军则因为与浙军有争斗,驻守在通州时已有火并,两方炮击对方,死伤遍地。所以,指望三支部队齐心协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不相互打起来就已经是万幸了。
正因为三军互不信任,所以他们的部署出现了大问题。自信满满的川军最先出发,部署在浑河北岸,离八旗军最近,浙军则部署在浑河南岸,与川军隔江而望,而辽军则部署在附近。三支军队虽未合兵一处,但距离不远,好歹可以呈掎角之势,然而他们互看对方不顺眼,导三军纷纷成为孤军。
战事未启,明军就已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霾。

一、白杆兵血战浑河北岸
穿过岁月的尘埃,我沉浸在辽宁沈阳浑河的浪花之中。那一波又一波的水浪拍打着堤岸,多少记忆纷至沓来。风从云层中旋转出来,告知一段悲壮的过往。
浑河,古称沈水、小辽河,历史上曾经是辽河最大的支流,如今是独立入海的河流,发源于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滚马岭。
据说其满语为“乌拉巴图”(笔者认为这是蒙古语,乌拉是河的意思,巴图是坚固的意思)。
在历史上,浑河两岸发生了一场大战,也就是刚刚崛起的后金(建州女真,后来的清)努尔哈赤与明军的血战,最终努尔哈赤惨胜,明朝威名远振的戚家军落幕。

努尔哈赤自起兵反明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明天启元年,努尔哈赤趁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去职,新上任的袁应泰无能,率八旗子弟攻打明辽东的卫城沈阳,辽东经略袁应泰发兵救援,以驻守辽阳的四川石柱、酉阳士兵七千八百人、戚家军三千七百余人,以总兵陈策,副总兵董仲揆,戚家军将领戚金,以及石柱白杆兵将领秦民屏、秦邦屏,酉阳将领冉文光等人,向沈阳进发,到达离沈阳仅十余里的浑河时,沈阳已经失守,原打算的与沈阳守军内外夹击的计划落空(仅仅一天就失守了)。
年已古稀的总兵陈策闻沈阳已经被努尔哈赤攻破,便决定回师。
随军的游击将军周敦吉等将领激情昂奋,一再请战,大家对陈策说:“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
于是,陈策与众将商议后,决定立营迎战后金人马。
游击将军周敦吉与副总兵、四川石柱都司佥书秦邦屏等将领率石柱、酉阳士卒七千余渡浑河,在河北立营;陈策与副总兵童仲揆、戚家军将领戚金、参将张明世等将领统戚家军三千余在河南立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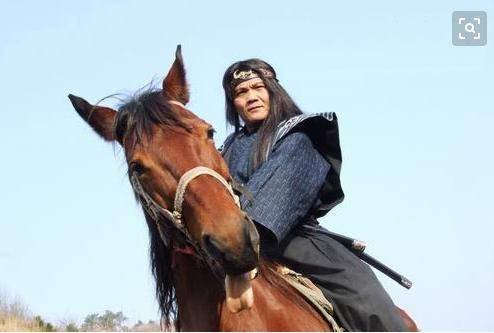
说来这石柱白杆兵是明朝著名女将秦良玉统帅的四川忠州石柱土司兵,号称白杆兵,是当时明朝的精锐部队,由其兄秦邦屏、其弟秦民屏率领,这白杆兵强悍善战,装备川东少数民族特有的利剑大刀和锋利的长柄竹矛,身披铁甲又外罩一层厚棉,刀箭不入。
努尔哈赤见这支明军不过七八千人,又皆是步兵,八旗军发起攻击,要一鼓作气拿下,而明军虽然人少,却组织严整,人不畏死,一接战就重创八旗精锐红巴喇军,败退下来,令努尔哈赤大吃一惊,努尔哈赤整顿人马卷土重来,白杆兵几次击退八旗的进攻,死伤惨重,后金参领西佛先,佐领席尔泰、格朗等人阵亡。
这也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遇到最强硬的对手,反复攻击都无法击溃这支明军。
努尔哈赤手下降将李永芳经过对明军阵地的观察,发现这支明军装备有战车、火器的皆在浑河南岸,北岸的明军只能依靠长柄竹矛和盾牌抵御后金铁骑,并且北岸的明军身穿重甲,不利于近身格斗,如果利用火炮将北岸明军阵地轰开缺口,后金人马冲上去便解决战斗。

当时,后金军队并没有装备火炮与火器,但李永芳知道,刚刚占领的沈阳城城墙上有明军的火炮。
李永芳一面报告努尔哈赤到沈阳城墙上取炮,一面找来被俘的明军炮手俘虏,给予重赏,让他们为后金效力。
很快,沈阳城墙上的那批小口径火炮运到两军阵前,放炮轰击河北岸的明军阵地。
白杆兵与酉阳士卒没有战车与火器的缺点显露出来,他们的冷兵器无法阻挡火炮的攻击,在炮火轰炸下,阵形大乱。
后金骑兵乘着烟雾杀了上来,明军不敌大败。
游击将军周敦吉,酉阳将领冉见龙,白杆兵将领秦邦屏,参将吴文杰等人战死,残兵在酉阳将领冉文光、白杆将将领秦民屏等人的带领下渡河撤离战场;参将周世禄也乘乱突围而出,邓起龙、袁见龙拼死夺桥相继返回浑河南岸戚家军的阵地。

二、浑河南岸戚家军落幕
戚家军布阵在浑河南岸五里许,外围环以战车,布列火炮火U,掘壕安营,用秸秸为栅,外涂泥巴,严阵以待。
后金兵马消灭了河北岸的白杆兵与酉阳兵,迅速渡河杀奔而来,数倍人马把戚家军围个里三层外三层。
当时北岸白杆兵、酉阳兵与后金人马血战之时,南岸的陈策、童仲揆就认识到事态严重,因为南岸仅有三千余人戚家军,赶紧挖壕立营,架炮环车组成车阵。
车阵是戚继光、俞大猷在实战中创造出来对付骑兵的战法。战车在行军时可以装载粮草军械,驻扎时可围起做营盘,防御时战车环形防御阵地,将火炮架于车上,士卒以车为掩体,利用火炮火矛杀敌。
这支戚家军是由戚继光的族侄戚金率领,戚金,字少塘,其父叫戚继明,他“少从少保(戚继光)戎,屡建战功,由百户历升守备、游击、参将”,戚继光去世后,戚金成了戚家军的真正统帅,升任副总兵。

努尔哈赤也认识到这支明军的厉害,北岸八千人就重创了八旗子弟,南岸这三千多人明军,有火炮战车,更不敢轻敌,再三告诫手下,切勿轻敌。
努尔哈赤对戚家军形成合围之后,以四旗的优势兵力从左翼发起攻击。
总兵陈策率领童仲揆、戚金、张明世等将领沉着迎战,誓与后金决一死战。
当后金人马进入有效射程,火炮与火焰齐发,给予后金人马杀伤。努尔哈赤两轮进攻死伤达三千人左右,努尔哈赤立刻改变方式,不再采用骑兵冲锋,而是将攻城用的战车推了出来,改骑兵为步兵猫着腰在后面,有效地防御戚家军火器的杀伤,而戚家军这边并没有装备足够的火药,很快用尽,自身的优势顿失,后金人马蜂拥而上,两军犬牙交错,展开了短兵相接。
战斗十分惨烈,戚家军全是步兵,又没有弓弩、沙袋,他们持着竹杆枪和腰刀,以哨为单位组成鸳鸯阵与后金人马展开惨烈的肉搏,每个队形中狼子手、藤牌手与刀手相互掩护配合,有效地杀伤敌人。

太阳西下,夜幕降临,优势兵力的八旗子弟并没有占到半点便宜,一时间胜负难分。
然而冷酷的现实很快让戚家军陷入困境,后金增援的兵马赶到,让本来就处于劣势的戚家军很快就被后金人马分割瓦解,陈策斩杀了十余后金人马,壮烈殉国,而三千多戚家军几乎都阵亡,后金兵马对着残存的戚家军万箭齐发,童仲揆、戚金、张名世、袁见龙、邓起龙等将领皆战死,戚家军全军殉国 (与后金兵马鏖战之时,陈策派人向袁应泰叩首发兵救援。袁应泰早就被如狼似虎的八旗子弟吓破了胆,竟然以后金兵马强大,派兵也扭转不了战局为由拒绝发兵)。
戚家军自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建军,剿灭倭寇,痛击蒙古铁骑,赴朝抗倭,百战唯浑河一败,明军数锐尽失,全军覆没,终成绝唱,从此世间再无戚家军。
就在戚家军与八旗人马血战之时,明朝总兵李秉诚,将领朱方良、姜弼等人率领的三万援军已经到达距离浑河只有十余里的白塔铺。令人愤怒的是,李秉诚等名将即没有增援戚家军,更没有采取行动,迂回到后金侧后发起攻击,而是驻足观望,懦弱不敢接战。

当努尔哈赤得到有大股明朝援军到了白塔铺,着实吓出一身冷汗,如果这支三万人的明军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发起攻击,对于后金人马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努尔哈赤急忙派儿子皇太极率几千骑兵去阻截这支明军。
这个李秉诚十分可耻,面对皇太极的几千人马,并没有迎战,带头就跑,皇太极一阵追杀,让李秉诚损失了几千人马。
明朝与后金浑河之战,后金付出惨重的代价,损失了雅巴海、布哈、巴彦等战将和上万士卒,惨胜明军。明军万余人 (白杆兵、酉阳兵七千八百人,戚家军残部三千七百余人)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幸运突围返回辽阳,损失以总兵陈策为首一百二十余将领。
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过去以少胜多的他们这一次以数万人,分别两次进攻只有四五千的川军和三千的浙军,竟死伤数千人,可谓“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连努尔哈赤在战后也是心有余悸,为川军和浙军的勇悍所震惊。
这一战,数千精锐白杆军和仅剩的戚家军全部损失殆尽,然而,这个结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说川军与浙军没有相互支援,旁边的辽军握有重兵,却隔岸观火,看友军的笑话。总兵朱万良的三万援兵竟为数千八旗军所败,而袁应泰竟然吓破了胆,在浙军屡次向他求援时拒绝支援。
壮哉川军,悲呼浙军,他们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与八旗军血战不退,全军竟无几人生还。他们打破了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在野战中让八旗军吃尽了苦头。若非三家互不信任,袁应泰无能,浑河一战,谁胜谁负,犹未可知。
假如戚家军火药充足;假如李秉诚率领的三万生力军投入战斗;假如袁应泰能够及时派出援军,假如……历史没有假如,只有赤裸裸的现实。

小编提示: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敬请转发和评论。
